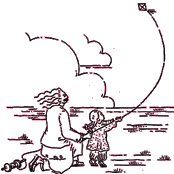我把这个用真实故事组成的花束献给你们——我的在美赫巴巴永恒爱里的世界家庭.漫步于童年记忆的花园里,我为你们采集了三十五个故事,每一个都散发着独特的芳香.
由于我写的是跟巴巴一起度过的童年, 自然这本书对孩子们有特别的意义. 但是我的书却不受年龄限制.这些故事中所传达的不老讯息是给所有的拥有一颗童心的人的.
藉着至爱巴巴的恩典,写这些故事变得惊人的容易.知道你的眼睛只会去看一个故事的核心, 而不会被时间和地点等问题所分散,对我很有帮助. 因为我想指出, 如果某件事情发生在1927年,而我认为它发生在1928年,这并没有改变那件事情本身,是不是?
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有关巴巴的书在日期等事情上会相互矛盾,即使满德里在满德里大厅讲故事时也会这样.你可能注意到我在这本书中所给的一些日期和细节与我之前在录音和录像中叙述故事时所给出的日期和细节有所不同。
我唯一所能说的是,即兴讲故事与深思熟虑后把故事写下来相当不同.我记得我的老师总是(用很重的鼻音)告诉班里的学生, “注意了孩子们,动笔之前要动脑.” 所以,在写《神兄》里的这些故事之前, 我做了很多思考,还做了不少调查.也就是说,为了使叙述尽可能精确,我研究了那些昔日回忆和记录.
至于作序,我被告知这是件艰难的事情.但这篇序却一帆风顺,就好像是畅游在湛蓝湖面上的一只快乐鸭子.就如同和你聊天一样——我所喜欢的事情.我可以一直说啊说啊,但是我不能,因为这里的故事已经迫不及待,要欢迎你进入很久之前的那个奇妙的世界.那么,如何停下呢?让我们做曾在美婼的阳台上做的:午饭时间过去很久之后,朝圣者围坐在她的周围,我们全都站起来,站在巴巴的肖像前,大声呼喊三遍:
“胜利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
神兄
你能想象记不得第一次见到巴巴的情形吗?唉,恐怕我是记不得了!我不记得是因为我是在刚刚出生几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巴巴的.
1918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普纳的大卫萨逊医院,在此之前24年,巴巴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作为一群男孩儿之后的唯一的女孩儿,并且在我最小的兄长出生四年之后才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是个备受欢迎的孩子.
我从来不会厌烦听母亲给我讲我第一次与巴巴见面时的故事. “告诉我. 告诉我,” 我会乞求她, “是怎么一回事儿?”
巴巴的原名叫默文, 但是家人都叫他麦洛格(Merog)——达里语中的爱称,那是我们在家里通常说的语言。(达里语是在伊朗的乡村间通常说的一种方言。据说在很久之前,达里语曾用作波斯的宫廷语言。)母亲会对我说我出生的时候,恰好麦洛格就在医院里.护士出来宣布 “是个女孩儿” 时,他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他一听到这个,就马上跑来抱起我,拥抱我,让我紧紧贴着他.由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新生儿在未清洗干净之前是禁止被抱的,我母亲在床上激动地大声说: “别,别, 麦洛格,别碰她! 把她放下! 她还没洗澡呢!”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记得我刚出生时巴巴给我的那些拥抱啊!
不过,我却记得从我三岁起和巴巴在一起的童年时光.从可以追溯到的最早记忆开始,我就知道巴巴是上帝,并且他是我哥哥,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没有人需要告诉我这些.我知道这一点,就像小孩儿知道糖果一样自然.
这确实很简单.巴巴是我的哥哥,而他碰巧是上帝.或者说他是上帝,碰巧又是我的哥哥.
我对这个事实从来都不谦虚,从不。听到我的那些天主教朋友们谈论她们的教母和教父,我会亲口告诉她们,“没有人,除我之外没有人有神兄。我是全世界唯一有神兄的女孩!”
我还会让母亲告诉我,默文永远离开家并以美赫巴巴的身份开始生活时是个什么情形。她说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摇着我的摇篮,说我有多么的幸运。
我会要母亲一遍遍重复这件事情。“他说了什么,母亲?他离开家的时候,关于我,他都说了些什么?”
于是她会重复,“他摇摇你的摇篮,转向我说,‘她是多么幸运啊!’”
接着母亲会怅然地说,“是啊,玛妮,你确实很幸运,但我却不---因为你到来之后,我的默文走了。”我母亲非常爱我,我也爱她。但是她的这番话让我认识到她是多么最爱她的儿子啊,这总是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即使作为小孩儿,我也知道巴巴的爱是整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比其它一切事物都更重要. 对于我来说, 巴巴是第一位的;家庭,朋友,宠物,玩具则根据我当时的心情被排到第二或第三位。但巴巴总是第一。
即使是这样,有时候巴巴也不得不提醒我这个事实。在我的童年,有时候对某个不可企及的物件的偏爱,会蒙蔽我的首要选择。巴巴会以其可亲的方式向我显示,惟有他的爱才真正重要。他下降到小孩子的层面,寓教育于游戏中。那是让我铭记一生的教训;是只对他接受为门徒的少数几个人所做的游戏。
记忆中一个这样的事例是围绕着一辆三轮车展开的。我用一个小孩子的全部热情,垂涎邻居家的三轮车。它那三个小小的车轮纠缠着我幼小的心灵,以至于我一时忘记了谁才是第一。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岁。当时,我和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哥哥贝拉姆(Beheram)与阿迪(Adi)一起住在普纳的巴巴屋子。那时巴巴在孟买的大师之家(Manzil-e-Meem),那是巴巴培训门徒的第一个基地。我的哥哥佳尔(Jal)跟他在一起。
不管巴巴驻扎哪里,母亲总会带着我去找他。爸爸则留下,照看家和店面。我总是母亲去看她儿子的好借口,因为她也想和他在一起。所以,每当巴巴在孟买的大师之家时,母亲就会带我到那里看望。
在此之前不久,我们邻居家有个小男孩儿得到一辆三轮车。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可是从未见过三轮车,想骑在它上面的念头让人兴奋不已。我们会央求他让我们骑一下,可是那个可厌的男孩儿却叫着,“不行,不行。”他连碰都不让我们碰一下它!
日复一日,我想要拥有一辆三轮车的愿望也与日俱增。愿望越来越大,直至掩盖了其它所有的一切。在和母亲一起去大师之家的路上,我所能想的全是三轮车。我不住地自言自语,“我要向巴巴要一辆三轮车。他会给我一辆三轮车。”
小时候,无论何时去巴巴那里,我都会径直飞快奔向他。巴巴则会张开双臂在那里,搂着我。他会把我抱起来,拥抱我,同我一起玩,并把我放在他腿上。虽然年幼,我也知道我有多么幸运!
所以,当我又一次在大师之家,坐在巴巴腿上时,我告诉他,“我的生日快到了。”
“哦,” 巴巴说,微笑着,“你的生日?好极了!”接着他又给了我些拥抱,说道,“你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
这正是我所等待的。“一辆三轮车,”我答道。
“好,”巴巴说,“你会得到一辆三轮车的。”
我撅起嘴,“但是你会忘记的啊。”
巴巴显得很吃惊。“忘记?”他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忘记呢?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忘记的。”
但那对我还是不够。每个小女孩儿内心都拥有一点女人的狡黠,我要绝对保证——拥有一辆三轮车。
在印度有句与“我在胸口划十字发誓,说假话就死亡”的同义语。就是说,你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脖子(喉咙)的皮肤,说“卡萨姆(Kassam)”,意为“我发誓。”你以任何珍爱的事物发誓。你可以拿你的宗教信仰发誓,拿你的母亲发誓,甚至拿你的胡须发誓。你以对你最珍贵的东西发誓,冒着食言就失去之的危险。所以你瞧,没人能违背这样的誓言。
我家有用卡萨姆的习惯,我也想从巴巴那里听到卡萨姆。所以我继续撒娇,说,“你会忘掉的。”我低声坚持着,直到最后他说,“卡萨姆,”一边使劲捏住他喉头的皮肤。“我发誓我不会忘掉。我以一只母鸡发誓。”
我终于满意了。巴巴的诺言由卡萨姆这个动作所保证,那只母鸡就是见证.
我下一个记忆是在普纳的家里,我的生日很快要到了.只剩下寥寥几天了.我唯一能想的就是三轮车.每回有人敲门,我都兴奋起来.“一定是三轮车来了,”我想。“是佳尔或其他什么人带着三轮车从巴巴那儿来。”我会先于母亲跑到门口。却不是三轮车。是送奶人,或卖面包的,或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邻居。却从来不是三轮车。
我的第四个生日是在一片欢乐气氛中度过的。但它对我却毫无意义。我只记得整个期间我感到难过,但却不是因为三轮车。突然间,三轮车似乎不复重要了。我难过是因为巴巴不爱我了。他说过你若是爱某人,就绝不会忘记。但他却忘记了,他忘记了!所以,他不爱我了,不爱我了,不爱我了……呜-呜-呜……
下面我记得的是我和母亲在美拉巴德。我们到时巴巴在那里等着我们。他派一辆马车来接我们,我只是站在那儿,僵硬冷漠。巴巴走过来,把我抱起。我仍旧僵硬。他把我放在他腿上。我却没回应。他胳肢我,我没笑容。
他显得迷惑,问道,“怎么了?”
我不回答。我知道他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装作一无所知,说:“肯定有人对你做了什么。我在想那会是谁。是这个人吗?”
“不是。”
“是那个人吗?”
“不是。”
“我知道了。”巴巴说,因解开了这个秘密而显得释然。“我知道了。一定是母亲。她骂了你,也许甚至打了你。我去跟她讲明白。”
“不,不是母亲,”我说道,尽力忍着不哭。
“那么是谁呢?”巴巴问道。
我坐在他腿上转过身,指责地用手指点着他的胸。“是你!”我说道。
巴巴看上去很吃惊。“我?!我做了什么?”
接着,当然一切都道了出来,谴责和泪水。“你不爱我,”我哭泣道。“你说过你若是爱一个人,你就不会忘记。而你忘记了!你不爱我!”
巴巴抱着我,我一边大嚷:“你答应给我三轮车,但你却从未送来。你甚至发誓你会记住的。你以一只母鸡起誓!”
巴巴让我平静下来。然后他让我坐下,用胳膊搂着我。他告诉我,“你知道我爱你。永远记住这一点。我的确答应你,我不会忘记的,我也没忘记。我确实也以母鸡发了誓。但你知道那只母鸡怎么了吗?”
“不知道,”他的眼睛大睁的小妹妹说。
“那只母鸡死了,”巴巴说。“在你还没得到三轮车之前她就死了。所以你看,这不是我的错;这是那只母鸡的错!”
儿童的逻辑拥有未经常识推理所修剪的翅膀。巴巴的解释对我太有道理了。巴巴答应给我三轮车时,他以一只母鸡发誓。那只母鸡死了,诺言也不在了。你怎么能遵守一个已不存在的诺言呢?如果巴巴用来发誓的那只母鸡在我生日之前就死了,巴巴能有什么办法呢?是的,这全都是那只可恶的母鸡犯下的错!噢,如此的欢乐和安慰。巴巴没有忘记。巴巴爱我!
我从未得到三轮车。我也不再想要了。我唯一想要的是巴巴的爱,并且拥有了它。三轮车事件向我表明,被巴巴爱比世界上其它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包括三轮车。
跟巴巴一起做的教训游戏如同一棵小树般不停生长,并在适当的时候开花结果。三轮车风暴过去许多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巴巴并没有食言。当他用“卡萨姆”向我保证时,他所说的是,“我发誓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在假定他指的是三轮车。
没有,巴巴没有忘记。他爱我,对我爱得足以让我通过这次教训游戏记住:他是第一位的。
印度的风筝是用薄薄的彩色纸和一些细竹条制作而成的,风筝和一条看起来似乎有好几英里长的质地上好的细绳粘在一起.把细线固定在风筝上是个艺术,要求精确的平衡感.很多次,在放风筝前,我都会蹲在我的神兄身旁,看他用他那美妙的手指把细绳固定到一个新风筝上.
我对美拉巴德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巴巴放风筝.当时我大概有五岁.巴巴仍然在讲话,你在美拉巴德能看到的主要是破旧的军营和水槽.
无论什么时候母亲和我从普纳去看巴巴,我们都会在阿美纳伽(Ahmednagar)站下火车,然后坐着马车去美拉巴德.我们一到那里,我就会跳下车径直跑去找巴巴.一看到他,我会撒开小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奔向他.巴巴则会抱起我,拥抱我,并和我一起玩儿.
这个故事发生时,我们刚到美拉巴德.我到处寻找巴巴,可就是找不到他.最后,我看见他远远站在美拉巴德的宽广空地上.他美好的头发和白色的长衣(sadra)随风飘动着.
巴巴正在放风筝. 他身边只有帕椎(Padri)一个人,他站在巴巴身后不远处,手里拿着线辘. 随着帕椎为巴巴的风筝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线,线辘在他双手之间旋转着,快得不可思议.卷轴吱吱地响着,转得越来越快.
线也划过巴巴的双手,巴巴放的线越来越长,风筝飞得越来越高,直到它看起来像一只红色小鸟,在天上飞翔。它飞得是那么高,以至风筝线在接触巴巴的手处形成一个完美的弓。
巴巴低下头看着我。“你想放风筝吗?”他问道。
“啊,是的。”我答。在普纳时,我总是羡慕我的阿迪哥哥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放风筝,但我自己却从没能亲手放过。
“在这儿,握着它。”巴巴说,一边把风筝线递给我。我把它紧紧握在手中。随着风和拱起的风筝线的不可置信的拉力,风筝摇晃着,我抓着风筝线不放。过了一会儿之后,巴巴又把风筝接了过去。我兴奋异常,向别人炫耀我是如何放巴巴的风筝的。
年龄稍大后,我意识到是巴巴一个人在放风筝,尽管他让我相信是我在做。在我双手后面,是他在握着风筝线——不被我看见。虽然似乎我在驾驭着风筝来回移动,但实际上一直是巴巴在控制着它。
仍然如此。一个人认为,“我在做这。我负责那。”但在幕后,实际上却是巴巴在默默地做着一切——惟有巴巴负责——始终都是。
译自《神兄》(God-Brother—Stories from my Childhood with Meher Baba By Mani S. Irani,Sheriar Foundation,1993)
翻译:秋子 校对:田心 丽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