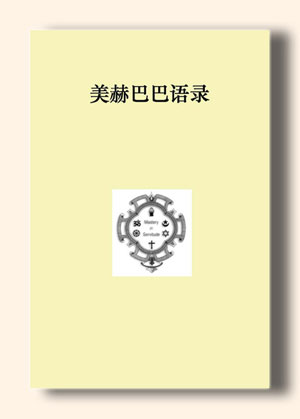1997年初,我同家人来昆士兰州度假,住在出国旅游的朋友家里,正好在基尔山上的美赫路,窄窄的石子路尽头是“阿瓦塔之寓”——1958年美赫巴巴的澳洲爱者专门为他第二次访澳而建的家。
一到,先生杰夫就立刻带我去巴巴的房间。这之前,我除了见过巴巴的照片外,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因为杰夫对灵性和宗教哲学感兴趣,多年来寻师访道,我嫁鸡随鸡,跟着参加过不同宗教的讨论课和静修班。这次也是出于礼貌才跟去的,心里还惦记着车里放了一整天的行李和食物。
等待我的却是决定性的:巴巴的房间像被充了电,空气高度凝聚,木制的墙壁散发出远古的玫瑰香。我感到身心无法承受,甚至有些窒息,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出去。
随后的一个月,我每天身不由己地往巴巴屋子的方向走,一进去就不断地流泪,仿佛几世的泪水都攒到了此刻。同时开始阅读有关巴巴的书,第一本是一对英国夫妇所著的巴巴传记《许多沉默》。读后第一个感想是,在我听说和知道的人里,美赫巴巴是最完美无私的。这样的人在世界上生活过,这个事实让我心里无比地满足。我甚至对杰夫说,还好巴巴已经去世,他不可能做也许会让我失望的事情了。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美赫巴巴著的《神曰》。至今还记得早上4点起床,坐在朋友家最东侧房间的地毯上,面对冉冉上升的朝阳读《神曰》时的喜悦心情。对于我,《神曰》不是为智力,而是为心灵而作的。伴着文字的节奏,我的整个生命不停地回应着: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合上书,我也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成信神、继而爱神者。
前不久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相信美赫巴巴?你凭什么确信美赫巴巴是阿瓦塔?”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认真想想,也许跟九年前的经历有关,但又不完全是。虽然在外部,巴巴那时才对我揭开他的面纱的一角,让我品尝了一点神爱的甘甜与苦涩,但他从一开始就是那么熟悉而亲近,我不可能仅仅在今世才认识他!
对于我,美赫巴巴是佛陀基督重临,就像蓝天白云是蓝天白云一样无疑;美赫巴巴是我的永恒至爱,就像我的父亲母亲是我父亲母亲一样自然。至于为何如此,也许只能借诗人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话作答:“因为信爱全凭恩典!”(for devotion is by grace alone!)
这些年跟巴巴在一起的生活,不全是“好玩”,也不是没有挑战和矛盾,但在品质上却不同于从前。巴巴说:“我不会改变你的命运,但我会给你内在的力量,去战胜生活的挑战。”在跟巴巴的神圣游戏里,他似乎有时呈现,有时隐藏,但他的“在”是如此地真实,有时几乎overwhelming(压倒性的)。
通过翻译《语录》和《神曰》,我慢慢地发现所谓的做巴巴工作,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以便帮助我们在服务中消除自我。有人说,越做巴巴工作,自我就越少。也本该如此!因为是巴巴在掌管着一切,支持着一切,做着一切。每次在我尽了最大努力后,巴巴总会打开一扇门——出乎预料、事后却感到理所当然的出路。《语录》初稿译出后,我没有把握,写信请教一位专事翻译的朋友,但他对灵性书籍不感兴趣。巴巴很快送来了一位中文教授兼求道者帮助润色。刚定稿,巴巴就派来资助者,出版者和印刷者。
2004年8月,中文《美赫巴巴语录》出版。澳洲的巴巴老爱者比尔和戴安娜夫妇到美拉巴德朝圣,拿着刚印出的第一本《美赫巴巴语录》到三摩地献给巴巴。就在比尔把书放在巴巴墓上的同一时刻,天上突然降下一阵骤雨,他们都深深地感到巴巴的祝福。需要指出的是,雨季过后的美拉巴德地区很少下雨,那天晴空少云,毫无下雨的迹象,且只下了那一阵雨。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三周前,有位亲戚说打算从悉尼来看我们,当天夜里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想送他一本《语录》,就去存放书的壁橱里拿,但每一本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上面写着不同的中文名字和地址。找了半天,却没有一本多余的。几天后,亲戚来访,读了我写的关于巴巴的一篇文章,说很喜欢。我随口说:“你喜欢,我送你一本《语录》吧。”他的回答是:“我现在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
看来,巴巴早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最初翻译《语录》,只是觉得这本书帮助我解答了根本的问题,译成中文,也许有一天国内有同样问题的人也会受益,根本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令人鼓舞的回馈。在此衷心感谢所有参与和支持过《语录》翻译和发行的朋友!感谢喜爱巴巴,喜爱巴巴文字的有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