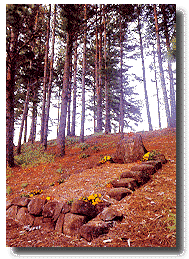(田心按:歌者写作的时间是2005年6月。1958年6月美赫巴巴第二次来澳时,曾在专门为他建造的阿瓦塔之寓住了三个晚上。巴巴说“阿瓦塔之寓”将成为世界性的朝圣中心。)
阳光海岸如此的美丽,由正在准备降落的飞机上看下去,变换的蓝绿之天、海、山, 飘舞的白云,让人相信那里是天上仙境。 而我此行的心境却绝非如此简单到可以用类似于美丽的一个词就概括的。
如果要说此行的意愿,WES比我要渴望得多。 鉴于以往的求师经历,我对于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某位神人是持怀疑及排斥看法的。
接待我们的田心夫妇是非常温和友善的人,一下飞机就直接把我们接往“阿瓦塔之寓”(AVATAR’S ABODE)参加巴巴来此地的47年纪念活动。汽车行驶在美丽的风景中,菠萝园被甩到后面,我想巴巴之所以选择了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它太美丽了吧。
阿瓦塔之寓占地两百多亩,附近住了很多巴巴的门徒,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FRANCIS BRABAZON,诗人, 原澳洲苏非团体的领袖) 将巴巴的房子建在了平缓的山顶上。 田心是位非常好的向导,为了让我们对整个阿瓦塔之寓有个了解,她 建议杰夫(GEOFF)先开车上去,她带我们徒步上去。
我们先看到的是弗朗西斯的墓。山坡上一片丛林之间,弗朗西斯的墓由未经雕磨的青石环绕着,经年落下的松枝掩盖着……让我本人也无法解释的是,从那一刻起,我对弗朗西斯产生的人类情感竟然似乎比对巴巴本人更浓烈。 那位辛勤地为巴巴建起寓所的虔诚的诗人,此时就歇息在这个远眺大海的山坡上。我似乎感觉到他的宁静的脸上带着微笑坐在那里,满足地陪伴着他的阿瓦塔之寓。
遗憾的是,我们的行程不允许我们在这里逗留很久,我想其他人也没有跟我一样对诗人有着惺惺相惜的类似感受,于是我们只是稍做停留就继续行程了。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
弗朗西斯之墓
下一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巴巴的阿瓦塔之居。
我受上任师父的影响颇深,到那时仍然对一切顶礼行为怀排斥态度,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姿态也是对自我存在状态的一种没有来由的崇拜和认可。 巴巴的房子先是一个长走廊式的外间,一头是弗朗西斯住过的狭小的房间(弗朗西斯受巴巴的邀请,跟巴巴和巴巴的门徒共同生活了10年,1969年巴巴去世后,弗朗西斯回澳,一直在这个小房间里住到1981年。他于1984年去世)。直到此时当我写到这里,都会为我所见的眼睛里噙着眼泪。这位伟大的人,他的房间小而简陋得甚至没有象样的床,而一张当年建屋时必有的工作台占据了房间一个角落。哎,弗朗西斯呀……
透过这个走廊式外间,会进入一个我认为是可以为爱者们(LOVERS)聚会用的厅。厅的一面就是巴巴的房间。现在的走廊式外间和内厅就具有展示功能。内厅至今还是爱者聚集歌唱巴巴的地方。中午时,会有人在此念巴巴的故事,来听的爱者沉醉地躺在地板上享受着巴巴的爱跟阳光一道撒满房间……
巴巴的内室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陈设,简单之极。 一张床、一张小桌,两张椅子,如此而已。房间由天花板到四壁加之地板都是木制的, 一种温暖的感觉。巴巴的座床上,如今放置着巴巴当年穿的一双鞋子。只一瞥之见,那双看起来如此普通的鞋子,竟然让人一下感受到了巴巴的存在。
我还是开了一个头,做了坚信不能顶礼膜拜的十年以来第一次的顶礼,但仍然心思纷乱。 虽然一进来我就一直有一种想流泪的感动,而眼睛里也是湿润的,但可见跟WES在一起的岁月我是有进步的,理性有所增长,对感情的控制也好多了。然而也许并非如此就好吧,呵呵。此后的时间里我似乎一直是在感受和理智之间心乱而摇摆,也许因此而丧失了一次机会。
由于我们本来就来晚了,而本日的行程又很丰富,所以,我的第一次顶礼就匆匆结束了,虽然我心里好想在巴巴的房间里坐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里,田心热心地帮我们介绍那些曾经见过巴巴的人,听他们讲述当时的故事,籍此感受着巴巴,并忙于参加各种爱者们的活动,我坚持着不提出想去巴巴房间独坐的想法,应该是自己感性和理性的挣扎(感受到与巴巴的靠近和对神人的理性质疑)吧,直到当天结束。哎,也许我太愚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早早就出发了,听说有丰富的印度早餐等我们呢。在路上我又很谦虚地跟田心提出想在巴巴房间里多坐一会的建议,杰夫慷慨地说可以呆上半个小时……我晕……呵呵。田心和杰夫尽心地当着我们的东道主,而且做的如此周到。他们尽量想让我们获取更多的信息,我想他们并不了解的是,我很想直接与巴巴沟通,但其实那个时候,出于一种对“个人崇拜”的抵触情绪,甚至连我本人都不了解我的这个渴望,又怎么能让别人了解呢?
事情终于发生了。早上是例行的阿提(ARATI)。 爱者聚于巴巴的房间唱颂着美丽的赞歌,临近结束时照例是80多岁沉默寡语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第一个默默地走到供放着巴巴的鞋子的座床前,顶礼下去。当他站起来时,80多岁的老人显得有点吃力,所有的人都会想去帮助他,而此时所有的人都怀着敬意沉默着,老人专著地缓缓站起来。啊,当你看到一位追随巴巴多年的80多岁老人如此沉默地爱着巴巴,当你看到一位老人为巴巴落泪,除了感动还会有什么呢?
爱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顶礼后退到外面的厅里去唱赞歌。我想我是可以实施杰夫承诺我的半小时时间了。所以我坐下来,以西方人不太理解的“静坐”方式无意识地开始与巴巴的沟通。 遗憾的是,由于与之前的各种“个人崇拜”观念的挣扎, 我此时的心境还是乱如麻的,但我清楚地感受到一种渴望,想与巴巴沟通的渴望。 于是我坐着。
慢慢地,我周围的世界离我远了些,我开始了那种心乱中的感受:巴巴与我。 其他的赞美的歌声、窃窃的私语、崇拜者的礼拜,发生着却与我不甚相关。我开始感受到巴巴与我的存在,其他的开始些许地剥落成与我无关的戏剧,发生着,但与我无关……如果不是由以往的经验所造成的对于“个人崇拜”的排斥,而此时这种排斥带来疑惑和纷乱,我想我的那种与巴巴一起的体验会更深些。就这样,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中,我追逐着那种与周围剥离的与巴巴共存的状态,坐了一段时间,众人散去了,我想也许我该去参加活动了,以免因为我影响大家的活动。但这个想着“大家”的决定似乎是错误的。
我起身跟WES和田心一起,准备按照计划去参加戴安娜.拉裴基(DIANNA LE PAGE)的巴巴画展。但是此时我无法专著于周围发生的任何事,不想与任何人交流,也无法与人进行普通的交流,无法理解并融入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去,我只想沉默,只想回到巴巴的房间。终于在我们沿着弯曲的山路到达戴安娜的画展后,我成“玛司特”(MAST)状了。戴安娜很友善地跟我拥抱迎接我,说:我真高兴你能来。而我脱口而出:我只是想看到每一张巴巴的像而已。 太不礼貌了,但那的确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看着巴巴的画像,一种绝对的崇拜感受占据着我的心,让我再也无法继续这种正常的交往活动,只想回到巴巴与我的状态,我实在忍不住向着巴巴的像顶礼下去,然后决定会巴巴的房间。
我一个人跑了回去,一头钻进巴巴的房间,(现在想起来真感谢WES没有找我。)开始向巴巴祈祷:“巴巴啊,请求你给我完全示现那个真实的存在吧,让我看清楚这个世界的幻想,我求你!”我的心更乱了,甚至没有了之前的那种与巴巴同在的感受,能做的就是重复上面的祈求。我想,既然我们听到那么多的故事证明了巴巴是无所不知并能给每个渴望以答案的,我现在就坐在他的房间里,为什么他就不能答复我的祈祷呢?为什么??也许是我的时候未到吧,呵呵,我被送了回来,只瞥到了一线真实和幻想之间的缝隙,连神圣的疯癫的边都没有达到就被送了回来。:)遗憾!
等我再起来的时候,田心、杰夫、WES和JEHANGIR正坐在那边聊天。而我此时已经恢复成了正常人。哎~~~不划算,没有当成他们取笑我的“玛司特”不算,我还错过了据说不可思议的印度早餐,还有午餐。好在我没有错过晚饭。
晚饭前是传统的度内火(Dhuni)。巴巴曾经让他的爱者每人将一根木棒扔进火里,代表着将自己想驱除的某个东西扔到火里,巴巴会帮助他/她实现这个愿望。很多的故事证明这样做的灵验。后来我们告诉SAKSHIN此事,并讲了一个人因为不知道要扔掉什么而随便烧了一张纸币之后便开始破产的故事,SAKSHIN竟说他想把他家的贷款合同烧了,哈哈哈哈……
吃晚饭的时候,突然一个爱者手里端着一个盒子走过来说:“有人没有抽过巴巴的语录吗?”田心告诉我说是每个人象抽签一样从盒子里抽出一张写着巴巴的话的纸条。因为我中午没有来吃饭就错过了。于是我抽了一张,上面写着巴巴的这句话:“The ideal prayer to the Lord is nothing more than spontaneous praise of His being.(真正的对上帝的祈祷是对上帝存在的由衷赞美)” MY GOD!想想看我的感受。正是中午的那个时候,我正坐在巴巴的房间里痛心疾首地向他祈祷着要他示现给我那个真实的存在,并质疑着巴巴无法给于我传说中他总是给于每个渴望的答复。而我投入度内火中的,也是我对真实存在的无知。此时,他难道不是在对我讲述吗?
其实写到这里也就不必再写了,对我而言,此行的目的无非如此。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我开始爱上巴巴,并同时经由这种爱我以人类特有的“质疑的头脑”逐步认识着那个传说中的真实的存在。JAI BABA!
巴巴的房间